倒行逆施的惡果
如影隨形的飢荒危機 聯合國多年努力付之一炬
文/呂佳恩
2015年,聯合國啟動17項永續發展目標,其中一項方針是在2030年前,確保世界上所有人全年都有安全、營養且足夠的糧食,並消除所有形式的營養不良。著眼當下,15年已過大半,我們是否逐步接近著這令人敬畏的目標?
2022年6月,聯合國五大機構共同出版《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》報告,內容顯示,2021年全球飢餓人口攀升至8.28億,其中,有4,500萬孩童患有消耗性營養不良(wasting),面臨發展遲緩或甚至死亡的風險。展望2030年,仍會有6.7億人繼續與飢餓共存,值得注意的是,這與2015年的數字相去不遠,意味著聯合國多年來的努力,最終將會付之一炬。
然而,回顧過往十年,農業生產的技術大幅進步,全球穀物產量增加了17%,全球人口數則只成長6%,顯然糧食產量並非問題所在,真正的關鍵,是糧食分配不均與極端貧困帶來的飢荒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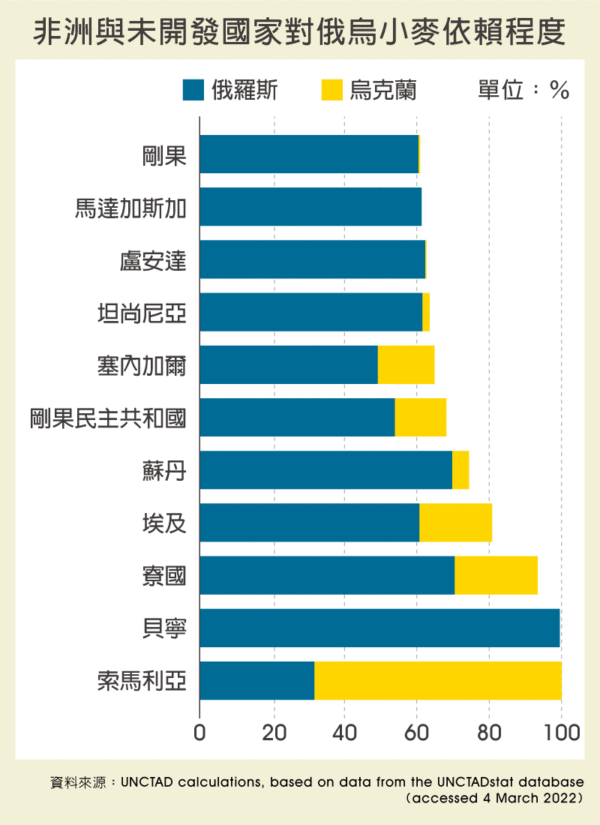
世界糧倉冒硝煙 落後國家成犧牲品
2020年,新冠病毒強勢襲來,許多人甚至頓失經濟來源,加上供應鏈及物流惡化一步步推高物價,全球飢餓人口大增。疫情肆虐快3年了,儘管全球已能用和緩方式因應,但飢荒猛獸仍未停止壯大。2022年2月,俄羅斯總統普丁下令揮軍烏克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,戰爭硝煙壟罩烏克蘭上空,全球市場瞬間受到衝擊,全球經濟尚未完全復甦,再面臨嚴重威脅。
在俄羅斯的封鎖下,烏克蘭的糧食出口遭封鎖長達五個月之久,大幅依賴烏克蘭穀物的低度開發國家,成為這場無情戰火之下的犧牲品。
烏克蘭擁有全球25%的黑土,得以孕育出玉米、黑麥、小麥等主要農產品,細看該國的出口名單,最主要的玉米買家是中國、荷蘭等國,然而,儘管無法取得烏克蘭的供應,這些富裕國家也能轉向其它地區,以更高的價格購買糧食,但對於經濟早已步履蹣跚的發展中國家而言,失去烏克蘭的供應無疑是一場生存危機。

根據經濟複雜性研究中心(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)的數據,北非突尼西亞大約70%的穀物依賴進口,該國主食以小麥、麵包為主,其中,近48%的小麥皆源自於烏克蘭,也因為這樣的依賴性,在俄烏戰事推升糧價後,突尼西亞原已搖搖欲墜的糧食體系幾近瓦解,同樣位於北非的摩洛哥與埃及也沒躲過這場劫難,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報告,埃及逾70%的人口,已無法獲得營養的飲食。

麵包革命浪潮未遠 爾今危機四伏
綜觀阿拉伯世界,社會與經濟問題並非憑空出現,過去14年前來,該地區始終危機四伏。
2007年至2008年間,糧產被轉於用作生物燃料,助推全球糧食價格遽升,全球48個國家發生暴動,突尼西亞也在其中。緊接著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之下,突尼西亞的失業率在2009年攀升至13.3%,該國經濟落得如汪洋中一艘扁舟,載浮載沉。
2010年,全球小麥產量銳減導致價格大漲,飲食大幅依賴粗粒小麥粉的突尼西亞再次遇難,經濟重擔與累積已久的腐敗政治引爆了民怨,最初被稱作「麵包革命」(thwart el-Khobz)的抗議,最終在全國開出一朵朵的花,演變成全面性的「茉莉花革命」(Jasmine Revolution)。這股自由氣息吹向整個阿拉伯世界,帶領阿拉伯人起身反抗專制政權,造就了「阿拉伯之春」(Arab Spring)。
然而,民主的道路遠比想像中崎嶇。這股春意並未維持多久,凜冬便再次吞噬阿拉伯世界。埃及在穆巴拉克下台的兩年後便遭遇政變,塞西上台執政至今,一日日越加獨裁;利比亞告別強人格達費,長年深陷混亂局面;敘利亞更是陷入內戰,從前的文明古都,淪為戰火煉獄。
而回頭看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地突尼西亞,雖然民主之風成功吹倒威權,卻始終無法孕育出繁榮的種子,2021年底,突尼西亞政府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(GDP)的比例已攀升至79.7%。

中東擁天然資源 最富有的窮糧之國
阿拉伯之春轉眼間已是十多年前之事,平等的社會與安穩的政治環境卻似乎越來越遠,中東地區雖坐擁豐富天然資源,人口數僅占全球6%,然而身陷糧食不安全(food insecurity)的人口數卻是全球的20%。2020年,新冠病毒一場暗襲,讓全球經濟一下子亂了調,阿拉伯地區的經濟危機再度惡化,部分國家採取財政刺激政策及超寬鬆貨幣政策,連同囤貨及出口限制,導致物價飛漲。
人類至今尚未戰勝病毒,但氣候變遷引發的極端氣候再次重創北非,使其面臨嚴重乾旱,糧食產量銳減,緊接著俄烏戰事展開,全球穀物價格遽升,早已債台高築的突尼西亞政府無力支付小麥的運輸費用,致使國內的食品價格暴增19%,麵粉和粗粒小麥粉陷入嚴重短缺。
突尼西亞的窘境,其實就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縮影,聯合國緊急應變小組的報告指出,中東及北非地區共有八個經濟體正面臨嚴重的能源及財政危機,儘管該地區有數個石油出口國,然而龐大的貧富差距導致底層民眾難以負擔高油價與物價。聯合國預估,中東及北非地區今年將有280萬人落至貧困線以下,意即每日生活費低於1.9美元(約為新台幣60元)。
乾扁的荷包、空著的餐桌,民眾不得不在兩條道路之間做出選擇:移民去歐洲,或起身反抗。在物價壓力緊逼下,民眾積累多年的怒氣衝破臨界點,埃及、突尼西亞、伊拉克、巴勒斯坦等國陸續爆發示威遊行,阿拉伯之春彷彿再度重演。
然而,物價危機並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一道難題,也是已開發國家的一根芒刺。
2022年2月,英國智庫UK in a Changing Europe發布了一篇報告指出,在不納入疫情造成的影響下,2019年底至2021年9月,英國食品價格因脫歐後的貿易障礙已攀升了6%,俄烏戰爭爆發更是加劇了物價危機,民眾在超市結帳的金額較一年前增加了13.4%,雞蛋、牛奶、起司等產品更是上漲22.1%,以光速飛漲的物價最終將英國人也推上了街頭,多個工會醞釀罷工,要求資方提升薪資,而同樣的情景,在法國、德國也陸續上演。

惡性循環難關多 飢餓問題仍待拆彈
過去五個月,雖然全球糧價指數逐步走跌,然而糧食危機並未真正解除。極端氣候來襲、化肥供應吃緊,全球糧食供應未來仍有重重難關,聯合國預估,在最壞情況下,全球糧價在2027年前會再漲8.5%,對於新興國家而言,無疑是一大噩耗。
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2022年8月報導指出,全球已有逾60個國家難以負擔農產品進口的費用,甚至有部分國家面臨債務違約風險,國際金融協會也於9月表示,糧食價格上漲對新興市場相當不利,目前全球已有35個國家深陷嚴重的糧食危機風暴,其中16個國家正面臨高債務風險,在在加劇了民眾取得糧食的困難度。
聯合國的「世界糧食日」即將於10月16日到來,2022年的主題被訂為「不讓任何人掉隊」(Leave NO ONE behind),聯合國盼能牽起每一雙手,走向沒有飢餓的世界,然而,現實遠比想像更骨感,戰爭、氣候危機、貧富不均等種種問題日益激化,其實早已將飽受飢餓之苦的八億人,遠遠拋諸腦後。
只是,面對俄烏衝突推升的惡果,科學家及國際機構並非沒有提出警告,貪得無饜的戰火可能會將新興市場與貧窮國度推入深淵。當人們忙於探討這場戰爭是如何威脅著全球脆弱的經濟復甦之路,如何深化強權對峙的格局之際,我們也該明白,這些其實並不是唯一值得關注的焦點。因為飢餓與流離失所,此際正威脅著世界另一個角落的人們。
